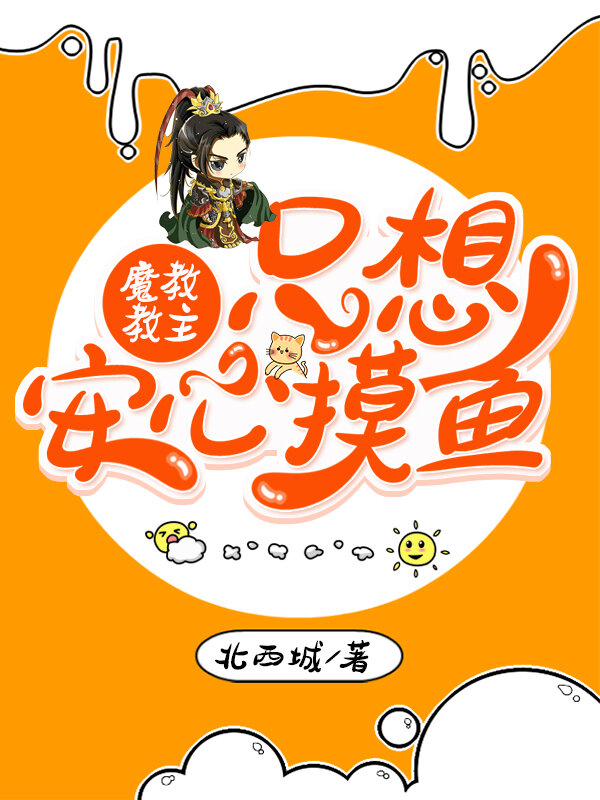
-
魔教教主只想安心摸鱼
第三章 我被威胁了?
时越连滚带爬地离开了书房,拎着两条有些发软的腿跑回了自己住的那个小院子,心里盘算着这魔教教主得赶紧辞了,迟早得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
她一进门就碰上了萍儿,萍儿见他面色苍白,像是又回到了之前大病时那股毫无生气的样子,忙上前扶住他,问道:“公子,你这是怎么了?方才王爷为难你了吗?王爷以前待你不是一向很好吗?”
时越摆摆手,“没事没事,可能是之前生病没好利索吧。”她不论是前生还是今世都不是那种轻易就感情外露的人,即使真受了什么委屈,也是吞进肚子里默默消化,不会哭闹着大肆宣扬。
萍儿明显不放心他,“公子当真不要紧吗?需要萍儿去找郎中吗?”
时越勾起一个笑容,“你可快饶了我吧,找个大夫来又要灌我喝那黑乎乎的药汁了,我可受不了,若姑娘是真担心我,倒不如陪我先谈几句。”
萍儿听他还能玩笑几句也就不担心了,说道:“公子想说些什么?”
时越坐下来,正色道:“王爷是个什么样的人?”
萍儿奇道:“公子与王爷相交甚笃,不是应该比我更加清楚吗?”
时越苦笑一声,道:“王爷胸中沟壑岂是我能看得分明的,只是想听听旁人的说法罢了。”
萍儿:“王爷是个好人,不仅相貌堂堂,一表人才,为人也很是光明磊落,知道他的人没有一个不称他一声君子。虽然他年纪轻轻,但是身上已有赫赫战功,当初他十七挂帅,平定西南,大捷而归,才把这世袭来的靖安王当稳。”
“王爷唯一不好的一点,其实也不能说是不好,就是……他对人都格外冷,几乎没什么见他笑过,不过这也不奇怪,王爷自幼丧母,后来又被那西域魔教害了父亲,活得未免有些寂寥。”
时越点点头,好在这剧本虽然不大一样,但是好歹顾庭筠人设没变,是个被魔教伤害的可怜人,只不过这事和她一点关系没有,顾庭筠父王被害她还只是个籍籍无名的教众,后来这莫须有的罪名被按到她头上还要拜副教主和白莲花女主所赐。
综上所述,她这一趟西域魔教之行除了辞职教主之外,还要想办法澄清她和老王爷的死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“萍儿,你可否帮我收拾一些盘缠,过两日我有要事需要外出。”
“好。”这姑娘很是机灵,平时与她亲近,但真遇到事情也不会盘问得过于细致。
时越脑海里徘徊了一万种小说里常见的男主发神经刁难路人的桥段,为自己的前途感到十分担忧,生怕王爷千机心脑子动太多她一句话说错就被砍了脑袋。
然而倒霉事总是比想象中来得更早,第二天时越就宗林带进了门口一辆豪华马车里,顾庭筠正闭眼端坐在马车里,整个人包裹在厚厚的狐裘里,显得一张脸有些尖削。
时越骤然一看见他顿时有些手足无措,既不敢离他太近,又不能太远,因为马车的空间也不允许她离得远,于是便僵成了一个被车顶封印的鹌鹑。
顾庭筠听到动静睁开眼瞟了她一眼,道:“你打算一直站着?”
时越尴尬地咳嗽一声,在门口找了个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下,避开了顾庭筠仿佛有实质的视线,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
“你好像生了一场病之后很怕我?”
时越讪笑道:“鬼门关走过一遭很多事情和以往有所不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”
顾庭筠嗤笑一声,说道:“呵,最好是吧。”
时越不明白他说什么,也无心多问,眼观鼻鼻观心地再次缩成了一个鹌鹑,不欲与他有再多的交谈。
顾庭筠也没再发问,继续闭目养神去了。
时越这一路虽然面上没表现出异色,心里却是翻了天,生怕这冷面阎王似的王爷找个野坟地把自己杀了祭天。
过了大约半个时辰,时越维持一个如坐针毡的姿势分外辛苦,几乎感觉身体有些控制不住的发颤,心想怎么还不到,不会真是荒郊野岭杀人放火的好地方吧。
马车停下来,顾庭筠这才睁开眼睛,说道:“到了,下车。”
时越赶忙爬起来,不小心撞了脑袋也硬憋着一眼框泪花迅速出了马车,她一下车当即打了个寒颤愣住了,她这嘴或许是真的开过光,眼前这一片肃杀也只有坟地能展现出来了。
“他费这么大功夫真是为了找个地方杀我?”时越不禁自言自语道。
“说什么呢?嘀嘀咕咕惹人厌烦。”顾庭筠也跳下车来,径直向前走去,“跟我来。”
时越看着他的背影好像没有黑气缭绕,堂堂一个朝廷权贵杀个贫民管杀不管埋也很正常,没听说过男主角还要给疑似反派的人物找好坟地的。她用蹩脚的理由安顿住了自己,忙跟了上去。
这墓地修得倒是有些像现代的公墓,大家一人一个小盒子,只留一块统一样式的墓碑记录墓主的姓名和简要生平。
顾庭筠走到最里面的两块墓碑前停了下来,时越在他身后两步的地方停了下里,顺着他的视线看了看那两块墓碑。那两块碑与旁人的倒是不同,白玉质地,精美异常,时越认不全上面的字,但也认得“顾”字。
顾庭筠问道:“你可知道这是何人之墓?”
“想必是令尊令堂。”时越看不到顾庭筠的表情,但是相比也不会心情好,小心翼翼地回答着。
顾庭筠:“不错,你可知他们因何而亡?”
时越斟酌片刻:“听闻是被西域魔教所伤。”
顾庭筠猛地回过头来喝道,“听闻?好一个听闻,呵,你当真不知情,当真没参与?”他似乎也不想听辩解,接着厉声说,“那天你一番胡言乱语打发本王,如今在这数千名丧生你魔教的英烈亡魂面前,你还有何颜面昧着良心胡说!若是你今日道出实情,本王可以给你留具全尸!”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