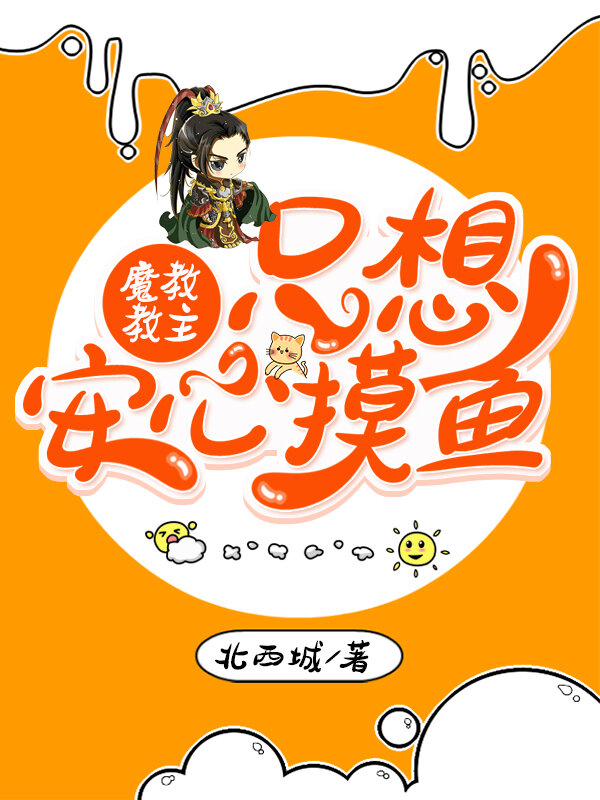
-
魔教教主只想安心摸鱼
第六章 我被他救了?
顾庭筠抓她的手力道不由自主地放轻,只是皱着眉疑道:“你真的不会武功了?”
“不会了,我从未对王爷撒谎,王爷信便信,”她顿了一下,深深地看了顾庭筠一眼,又扭开视线,像是很困倦的样子,“王爷不信便放开我,容我回去换身衣服陪王爷出征。”
顾庭筠皱着眉放开了她,时越低下头用脏兮兮的袖子抹了下眼角,低下头脚步虚浮地慌忙走了。
顾庭筠一瞬间竟然觉得自己有些过分,如若不是他多疑,时越完全可以免遭这些罪,但也不排除这人是在用苦肉计的可能,总之很多事情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。
韩魏上前说道:“王爷,我看他倒也未必说的是假的,西域之行还需三思啊,王爷位高权重,千金之躯,可万万不能出事啊。”
顾庭筠:“本王此去西域是收到消息,魔教教主在西域流窜,拉拢之前被我军打散的教徒,还妄图招兵买马扩大势力,此人一天不除,本王一天寝食难安。但本王此次离京之事万万不可让陛下知道,还望统领担待一些。”
韩魏曾是老王爷旧部,知道顾庭筠心中所想,老王爷和夫人丧生魔教手中,那是所有旧部心中的一块沉疴,小王爷能如此不忘先人遗志也是难能可贵,于是也便不再出言劝阻,算是应了下来。
时越回去之后,倒是把萍儿吓了一跳,一见他回来赶忙迎上去,担心道:“公子这是怎么了,一夜未归,王爷又闹出这么大阵仗真是吓死我了。”
时越没什么力气说话,只好冲她摆了摆手,便再次晕了过去。
等时越再次醒来的时候,天色已经暗了下来,屋子里没有点蜡烛,但依稀看得出屋子还是原本的屋子,看来本来预定的今日行程是没有走成。
时越觉得口中干涩便从床上坐起来想找水喝,她刚一坐起来,就有一只苍白的手举着一只白瓷杯子出现在她面前。
“啊!鬼啊!”时越没忍住大叫起来。
“你竟然说本王是鬼?”顾庭筠那一贯不冷不热的声音响起。
时越微微松了口气,擦了一把额头上被吓出来的冷汗,抱怨道:“你怎么在这儿?”
顾庭筠沉默了片刻,道:“刚才郎中来看过了,过度疲惫,又受了惊吓才昏厥,没有大碍。”
时越接过水杯一口喝光,心想古人的杯子就这么一点哪够喝,便起身把蜡烛点上,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,说道:“我知道,王爷不必担心,王爷打算何时启程再知会我一声就可以了。”
顾庭筠一张俊脸在摇曳的烛火中明明灭灭,表情有些说不上来的尴尬,过了许久他才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,说道:“抱歉。”
时越忽然觉得似乎这正好是个澄清的时机,清了清有些沙哑的嗓子,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真诚,她说道:“不怪王爷,要怪只能怪我不会武功吧。”
顾庭筠抬起眼眸,似乎依旧是不大信的样子,问道:“你当真失了功夫?本王未曾听闻有哪一种发烧能让人失去武功。”
时越知道他生性多疑,知道多说无益,便一耸肩,道:“王爷不信便算了,我若当真是魔教中人,又武功高强,便早就撺掇着王爷只身前往西域,顺便布下天罗地网恭候王爷了,又何必施展这一招苦肉计来哄骗王爷?”她顿了顿,喝了口凉茶,皱了皱眉,接着道:“再说,万一我机关算尽却弄巧成拙,王爷不带我前往西域,我又该如何自处呢?”
顾庭筠被她这一番现身说法说服了,她简直说得句句在理,令人无法反驳,他算是暂时勉强信了,“你……”他话刚出口又咽了回去。
时越一抬眼:“嗯?”
顾庭筠摇摇头,站起身,“无事,你休息吧。”
时越暗暗松了口气,知道这关算是过了,放在茶,拱手客气道:“恭送王爷。”
顾庭筠脚步一顿,说道:“以前你同本王没有这么生分。”
时越一噎,笑了下:“距离产生美。”
顾庭筠似乎是习惯她这种动不动讲几句疯言疯语的情况,也不在说话,推门走了。
时越又喝了杯茶才觉得舒服了不少,伸了个三尺长的懒腰,又捶了捶前不久被虐待得酸疼的腿。不过练武之人的身体果然是强健过人,恢复起来就是比常人快,回忆起当年她大学军训军姿站俩小时就腰酸背痛腿抽筋,现在折腾了这么多竟然也只是微微有些酸涩而已。
她站在窗前吹了一会风,觉得脑袋没有方才那么疼了,便又躺会床上,养精蓄锐。
等到第二天,顾庭筠才又让宗林来通知她后天启程。
时越有些疑惑地问道:“王爷不是很急吗?为何不是明日启程?”
宗林摇头道:“王爷的心思我做下属的可猜不透,倒不如公子亲自问问王爷?”
时越一想起那个活煞星的脸就觉得胃疼,忙摇摇手道:“不必不必,后天就后天。”
时越彻底翻了一遍这魔教教主的房间,竟然连一点多余的细软都没有,穷得简直倒立也倒不出一个钢镚,于是除了几件换洗衣服之外,她可以打包的东西大概就只剩下一个看起来挺值钱的牌子,牌子上写了几个繁复的字,但鉴于她本人是“文盲”也看不明白到底写了什么。
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极简主义吧。时越前一世出门前后俩大箱子,现在出门一个包,倒是省事不少。
等到出发的时候只有一辆看上去称得上破败的小马车,时越看着小马车犯了愁,顾庭筠在车里见她不上车,问道:“嫌弃?”
时越忙道不敢,心想只是不想和你离得太近,王霸之气太重容易误伤卿卿性命,最后还是上了车,努力和顾庭筠保持距离。
远方地平线依旧不见一丝光明,简直就是在合适不过的月黑风高杀人夜,时越不由得感觉有点冷,打了个寒颤。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