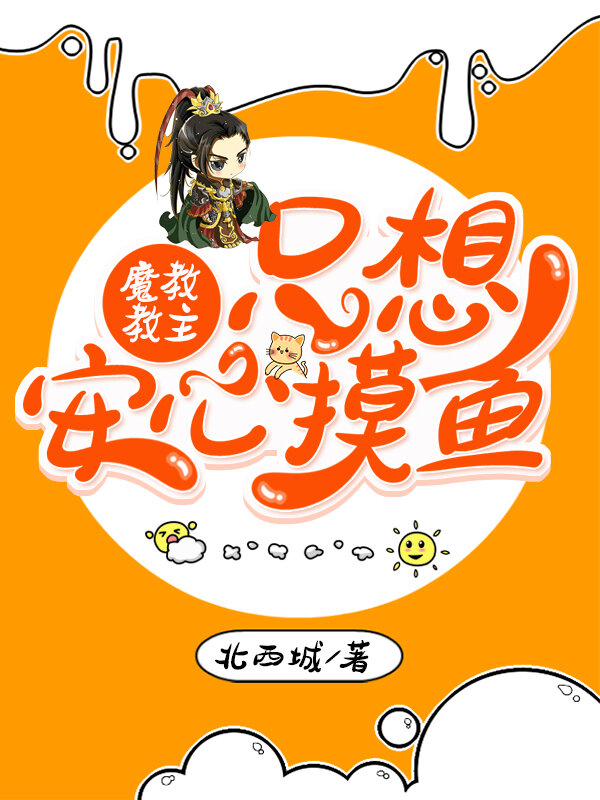
-
魔教教主只想安心摸鱼
第八章 我把他当猫?
顾庭筠没想到她还敢冲自己嚷,先是顿了下,随后说道:“你死不死和我有什么关系。”
时越抿了抿嘴,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,一把拽住顾庭筠狐裘领子,踮起脚气势汹汹地质问道:“我在你府上当门客,生了场大病,王府没医保就算了,烧没了武功还要陪你出来送死,你就这么对我!天理何在啊!”
顾庭筠被她吼得有点懵,半晌才恼怒起来,一把推开时越,扭头背对门,掷地有声地道:“滚!”
时越吼完自己这么多天来的委屈,觉得心里舒服了一点,心想自己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,多活这些天也是赚来的,便无所谓了。
临走前,她终于还是对着顾庭筠的背影说了一句,“你这样心冷的人,活该孤苦,我要是死了,你就一个人走这漫漫西征路吧。”
说完她便拍门走了,左转到了自己那间房门口,开了锁,利索地钻了进去,重重地关上了门,活像个闹脾气的小孩子。
顾庭筠半晌才转过身来,看着被时越拍上的门,心里莫名不是滋味起来。他出身皇家,原本该是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,却被伴君如伴虎的日子硬生生逼成了一个冷漠无情的人,天家无父子,更没有手足,能信的唯有自己罢了,旁人不过都是来来往往的过客罢了。
他回想起与时越初识时的样子,这人快意江湖,似乎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牵绊住爱她的脚步,即使无权无势、一介布衣,却可以纵览江湖,远比他这天潢贵胄身陷王府囹圄要强得多,这才起了把人弄回来当门客的想法。
如今虽然分不清这人说话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,但如此将人晾在一边似乎也不是很像样子,他思忖了许久,才终于下定了决心,推开门,却迎面碰上了提着两桶的热水的小二。
小二猛地和幕后大老板碰了面,一下子有些惊慌,随后忙道:“客官您若是有事要出去,那这洗澡水,您还……要么?”
顾庭筠顿了一下,随后说道:“提进来吧。”
小二:“诶,得嘞。”说完便招呼着身后几个小厮把一起提水进门,到了整整一个木桶,还讲究地撒了花瓣。
等顾庭筠一番沐浴,全身轻松地从浴桶里爬出来,才想起来时越的事情,利落地穿好衣服,简单擦了一把还在滴水的乌黑长发,才冷着一张脸出门,左转去了时越下榻的房间,抬了几次手,才终于敲响了门。
时越这边显然没有顾庭筠那么好的待遇,这才刚换了一副打算睡觉,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谁这么晚还会来敲门,她首先排除了顾庭筠那个混蛋。
莫非真是有人行刺?
她小心翼翼地靠近门,路过桌子顺手拿起佩剑,出了鞘,隔着门问道:“谁啊?”
顾庭筠深呼吸了一口气,不情不愿地回道:“除了本王还能有谁?”
时越先是一愣,顾庭筠不是刚才还又臭又硬嘛,怎么突然过来找她了?
时越把门拉开一条缝,谨慎地问道:“王爷来有何贵干?”
顾庭筠揉了揉眉心道:“你自己打地铺吧,本王今天睡这里。”说完便不听时越说话,强行推开房门,径直进了房间,坐在了床上。
时越:“???”
什么情况这是?
顾庭筠似乎丝毫不觉得有何不妥,看着时越一脸蒙圈的表情,挑眉问道:“你有什么问题吗?”
时越心想这死傲娇是突然后悔了吧,心里暗笑一声,最后忙摇头说道:“没有没有,没有问题,您请。”
顾庭筠听完满意地点了下头,打算拉开床褥打算睡了。
时越看着他的脸,还有些湿答答的头发有几绺服贴地黏在顾庭筠额角上,莫名地中和了他的锋利的五官天生带的杀伐之气,竟然显得有些人情味。
这作者还挺会写,要不是她看过原著知道这个男人一直是表里如一的杀伐决断,最后将魔教教主剁成肉酱喂了野狼,几乎都要被他此刻这点微不可见的善良骗过去了。
顾庭筠睁开已经闭上的眼睛,不悦道:“你还不睡?”
时越这才回过神来,说道:“睡,睡,这就睡。”说完才跑到顾庭筠的房间去抱了床褥过来打好地铺,吹熄蜡烛之前才和顾庭筠说道,“额,友情提示,头发不干就睡觉容易偏头痛。”
顾庭筠斜了她一眼,似乎在嫌弃她多管闲事,时越忙收声,“您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”
时越吹熄几处蜡烛,屋子骤然陷入黑暗,这动荡的一天才算是终于结束了,她如愿以偿得了个武艺高强的王爷排版在侧,倒是一夜安眠。
第二天早上时越一如往常是个起床困难户,即使身边有个活阎王也丝毫不能起到减弱她睡意的作用,于是她迷迷糊糊之间,感觉后腰有点疼痛,一开始并不明显,像是自家的猫在后背上不痛不痒地踩了几脚,随后这猫踩得越来越不知轻重,她迷迷糊糊喝了一声:“庭筠你别闹!”
那猫听话地停下了,随后腰后明明白白被人踹了一脚,时越这才清醒,一句国骂出了口,随后才反应过来不对劲,抬头一看竟然是真·顾庭筠!
时越揉着后腰,回忆起自己方才脱口而出的称呼,脸上青一阵红一阵,连准备好的质问也说得理不直气不壮,“你为什么踢我?”
顾庭筠俯视她一眼,问道:“你是猪吗?日上三竿了还睡?”
时越看了看窗外还只是蒙蒙亮的状态,顿时觉得无语,敢怒不敢言地爬起来。
时越洗脸的时候,顾庭筠才问道:“你方才叫本王什么?”
时越暗暗懊恼了一下,这家伙果然听见了,随后把脸上的水一抹,故作白痴样装糊涂,故意道:“啊?我叫您什么了?您听错了吧?”
顾庭筠冷笑一声,不再追问,扭头出了门,雪白的衣袍在空中留下一道残影,时越忙拿起佩剑和包裹追着他出了门。




